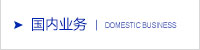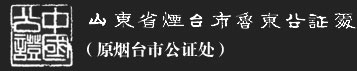小王于28岁去世,生前未婚无子女,生母在其5岁时去世,15岁时其父王某与年某再婚,二人共同生活1年、分居2年,后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小王遗留有房屋、银行存款遗产,王某称年某从未扶养过小王,二人共同生活的1年中,小王住校学习、回家时间较少,生活费、学费都由自己负担,年某无权继承小王的遗产,自己是小王的唯一法定继承人,向我处申请办理法定继承公证。小王的继母年某是否也是小王的法定继承人?根据民法典继承编相关规定,与继子女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是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可以继承其遗产,那小王的继母年某是否与小王形成了扶养关系?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的认定问题。
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形成的判定标准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学术与司法裁量观点亦不统一。目前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的认定标准主要有以下三项:
有扶养事实,继父母对继子女或继子女对继父母提供了物质支持与精神关怀、扶养费达到一定数额。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继子女跟随继父母生活时是否必须为未成年人?有学者认为继子女应当是未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无法独立生活,需要父母给予物质支持、教育引导、精神关爱。对于无法独立生活的成年继子女,因其已经成年不存在扶养问题,他们的照顾义务应当由其生父母承担,继父母的照顾应当认定为对其生活提供的帮助。然而司法实践中对于继子女跟随继父母生活时已成年,继父母持续为继子女支付生活费、学费与成年继子女对继父母长期予以照顾、年老时予以赡养的情况,也有认定形成扶养关系的案例。
继子女与继母或继父持续稳定共同生活,即扶养事实持续时间较长。
这里的“较长”应如何认定呢?曾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草案)中对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关系进行明确时规定:继父(或继母)和享有直接扶养权的生母(或生父)与未成年继子女共同生活三年以上,承担了全部或部分抚育费,付出了必要的劳务,并且履行了教育义务。该草案并未实施仅供参考,但由此可知,继子女父母扶养关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需要建立在长时间相互照顾、陪伴与支持的基础之上。
继父母与继子女的主观愿望,即双方均愿意建立扶养关系。
扶养关系成立需要尊重继父母子女双方的意愿,假如继父母对继子女成长提供物质、精神支持,本意是出于对其配偶(继子女生父母)的关爱,并非想与继子女建立扶养关系,年老时也不需要继子女赡养自己,那么应当尊重继父母的主观意愿。相反,假如继父母将未成年继子女扶养成人,双方已经形成了扶养关系,继父母年老时继子女应予以赡养,然而届时继子女不愿意维系与继父母的扶养关系,不履行赡养继父母的义务,也不宜认定双方扶养关系存续。此前因继父母对继子女提供了物质支持导致纠纷的,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我国法律尚未对继父母子女间扶养关系形成的认定标准予以明确规定,实践中应根据继父母子女共同生活的时间,物质供养、精神关怀的程度,结合继父母子女双方意愿综合判定。本文开篇案例中被继承人小王的继母年某与其共同生活仅1年,时间较短,年某也未对小王提供足够物质供养、精神关爱,故其与小王并未建立扶养关系,不能成为小王的法定继承人。我处受理小王父亲王某的法定继承公证申请后,与其前妻年某取得了联系,年某认可王某所述事实,认同自己与小王未形成扶养关系,并亲自至我处配合签署了询问笔录。王某作为小王唯一法定继承人办理了本次继承公证,单独继承了小王的遗产。